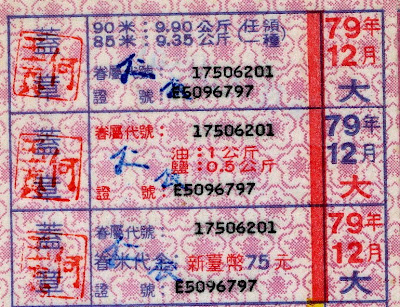二空組曲
王莉雰
暮色
依然是一個尋常的禮拜天中午,依然是一棟悠悠數十載、滿佈歲月滄桑的小屋,框著媽媽、舅舅、阿姨、侄子,也框住我和哥哥。
憶
四舅說:「記憶中,雙手呵護我們成長的母親,有著許多不同的形象,睜大著眼挑燈穿線串珠的母親,縫衣補綴的母親,擀麵做蔥油餅、涼麵、炸麻花、包子、水餃、粽子的母親,相同的是,母親一頭黑髮不知不覺中,已被歲月染成了了白髮。回想昔日,多少次陪伴著母親提籃上菜市場,有時拿著書,帶著小狗,陪伴母親散步……,景像清晰,彷如昨日。再回首,這些熟悉、溫馨的畫面,卻逐漸模糊、淡化,成了幻影。人生不能重來,再想重溫那些有母親陪伴的畫面,已不可得,方知人生最珍貴的不是財物,而是一去不復返、最尋常不過的情感。」
小舅說:「黎明的曙光照亮二空的街道,一群散步的婆婆媽媽們,遠望就看得出媽媽的身影—微駝的背、略胖的身軀及令人嘆為觀止的白金頭髮,永遠就是最好的註冊商標。慈祥的媽媽帶著滿臉的笑容,沒有怨言與倦容,用一道道菜伴著子女成家立業、傳宗接代,只盼一家和樂融融。唉,好懷念老人家用心做出的家常小菜,人間縱有千種美食,都比不上母親的家常小菜,,只因哪裡面多了一顆只求付出、不求回報的愛心」
二舅說:「『長勝,舖上睡』,一聲熟悉而親切的呼喚,驀然響起耳邊,猛然驚醒,卻遍尋不見母親的身影。猶記得年幼時調皮好動。每至晚飯後複習功課時,往往拿著書本念沒兩句,就不自覺的低頭猛點、睡意襲人。也許,由於父親身體違和、病痛纏身,母親更加關注子女的健康。在母親眼裡,一個發育成長中的孩子,疲了、倦了、睏了,自然就該去睡了,既打瞌睡,又想念書,是不自然、也不健康的行為。母親的呼喚永遠是那麼的溫馨慈祥,而今,自己已年逾耳順,孩子也大了,而天上的媽媽彷彿還在無休止的叮嚀,更深深地讓我體悟出「天下父母心」,念茲在茲的都是子女,只是…」
逝
沒有姥姥在的二空,連空氣都是破敗的。葬禮完後回到姥姥家,沒有了主人的它,失去了靈魂和生氣。窄小的屋子裡雖然擠滿了七個家庭的人,表面沸騰的人聲,掩不住潛藏底層的憂鬱,恰像皮球洩了氣似的,靜靜地往外溢,連溫度都低了一點。我站在院子一角,努力用回憶,阻止這正在消逝又無以名狀的過往,只是連回憶裡的晨曦都褪了色。
早晨七點多,爸爸把我包在被子裡,用車子載到隔壁巷子姥姥家。姥姥家緊挨著軍營後門口,營門在迎接完趕著八點上班的緊張人潮後,就由站崗的衛兵關上門。被爸爸抱下車、此時半睡半醒的我,總能隱約聽到各種鞋底蹬著柏油路的急奏。軍營大門輪子喀囉喀囉往前滑動的聲音停止後,也為這早晨的進行曲,畫下休止符。不願張開眼皮的我,總能看到一片螢光橘,出現在人聲倏地靜止後的我的聽覺世界裡,早晨的陽光舒服得很刺眼。把我放在姥姥床上後,爸爸才放心地去上班。那房間的味道像份量過重的安眠藥讓我沉沉地、徐徐地、毫無顧忌地飄進另一個美夢。
「妹妹兒,起得囉!」,煮好粥的姥姥,每天用著濃濃的四川口音在九點多叫著賴床的外孫女。即使擰乾了兒童專用的小毛巾往我臉上擦,那冰涼仍是不敵瞌睡蟲的頑強抵抗。每天早上,我就是在睡夢中被姥姥穿上衣服、抱下床,甚至也是在睡夢中被姥姥牽著,晃晃悠悠地走到路口的仁愛幼稚園。果真是要見到了老師,愛面子的我才自動轉換到清醒模式,開始三小時的學校生活。
夏天的中午,暑氣從柏油路上竄出,營造出一種海市蜃樓般的真實。姥姥有睡午覺的習慣。她總是讓我睡床的內側,自己睡在外側。還沒入睡的她拿著羽毛扇,搧著自己,也搧著身旁的小蘿蔔頭,試圖要趕走一絲絲汗流浹背後的黏膩。我總是會假裝睡著,偷看姥姥的睡姿,像在玩一種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遊戲,也訝異為什麼姥姥的身體這麼大,擋著我什麼都看不見。回想起來,那身體比高更筆下的大溪地女人更具有一種神聖的美感—是因為歲月鑿刻的皮膚?是因為老年人特有的緩慢律動?還是因為那有濃濃母愛的呼吸呢?稍長後,了解姥姥獨自揹負這龐大家庭的沉重擔子,我赫然醒悟,沒有姥姥山一般巍峨的身軀,如何遮擋外面的淒風苦雨,沒有姥姥海一般壯闊的胸襟,如何吸納外在世界的滔天巨浪?
就在姥姥離開的那年前後,二空開始有了改變。先是拆遷老舊房舍,再來是工程車進進出出。一層層的樓不斷疊高,突兀地豎立在平房為主的老舊街道上。大樓的外牆在太陽照射下意氣風發,毫不掩飾地訕笑著身旁不入流的老舊建物。我為這驕傲的態度感到氣憤,為了那被看輕的無語而失落。怎麼這樣一個空間的變遷,會讓我這麼難過和不捨?二空之於我有著什麼意義,它之於這個時代又有什麼意義?家又為何稱之為家?
從小在眷村被姥姥帶大,成天看著姥姥家附近小公園裡那群穿著白汗衫、拿著扇子和朋友聊天的老伯伯們,長大以後才知道他們是年少時兵馬倥憁、為國家拋下青春和親情的「老兵」。用一個名詞來統稱一群人總是讓我忐忑,人怎麼能以一個沒有生命的標籤去論述和評論一個群體?未免顯得高傲了。我也是到大了,才知道我成長的眷村是個特別的、充滿矛盾的生活圈,而「外省人」則是個很模糊的標籤,它指涉的既是難民,也是特權階級。且不論這一個個生硬的標籤,只要望向眷村裡每一個佝僂的身影,就無法漠視他們(她們)駝負著的顛沛流離和生離死別。如果有人願意去傾聽他們的故事,為他們刻畫生命群像,那成品定能在讀者心底衝撞出波瀾。他們惆悵、他們不安、他們不得已地在陌生土地上圍起竹籬笆,開始了一段在異鄉的日子。過了幾年,竹籬笆被紅磚牆和水泥牆取代,院子裡有了花草的顏色,小孩子們開始在「本省人」和「原住民」的圍繞下成長。那一點點的改建、擴建、裝飾、點綴、融入、衝突,都徒增了不得不的生存和切不斷的鄉愁啊!
在我心中,「眷村」是她,「家」也是她。姥姥離開後,我們還是有家族聚會。每個禮拜天回到斑駁掉漆的小房子,吃著媽媽和每個舅媽的拿手菜。舅舅們談論國家大事,晚輩們負責聆聽、受教。媽媽、阿姨和四個舅舅的聲音此起彼落,讓我想到童年時姥姥那張大床的氣息。沒有憂慮,沒有害怕,安穩和幸福原來是一種聽覺,可以是一種嗅覺。那聽覺延續著嗅覺,滲透在空間裡、聲音裡、食物裡、時間裡、破落窗櫺的木紋裡、鏽蝕大門的漆痕裡。原來眷村人的記憶和生命點滴,都收藏在那一間間不入流的平房矮屋裡。我也明白了自己對高樓的敵視,原來出自它們以入侵的姿態,竄起在不屬於我的記憶和生命風景當中。
如果問二空之於我的意義,我會說那是老爺、姥姥胼手胝足的侷限天地和希望,是媽媽、阿姨和舅舅們背著標籤、努力融入社會的胎盤和臍帶,它是我稱之為家的地方!而之所以稱之為家,是因為那裡的每一吋、每一秒被我們一起著了色、一起賦予了意義。它之所以稱之為家,是因為它牽動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共同記憶。以後在那些高樓裡,也會有人稱二空為家,但是他們看不到軍營大門前加緊腳步的人們、看不到家家戶戶曬臘腸的景象、聽不到水溝裡的青蛙在下雨天呱呱叫、聽不到各省鄉音在市場此起彼落、聞不到蔥油餅和烙餅那振奮早起人們的油膩、再也觸碰不到隨地取材就圈地成家的竹籬笆。我想像著他們未來記憶裡稱之為家的二空,然後閉上眼睛回想著小時候每個早晨刺眼的螢光橘。
夕陽斜射下的二空,新舊對立著、矛盾著。我想我還是喜歡早晨多一些。因為螢光橘褪色了,在人與物都顯得凋零的黃昏。